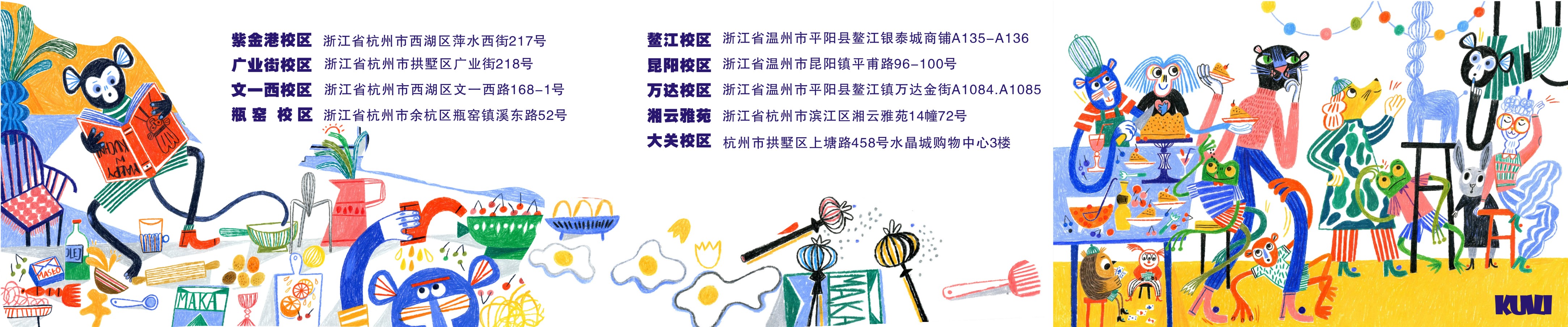报道转载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28705237
中国造神计划(GOD,MADE IN CHINA)是由青年艺术家崔绍翰、吴劭恩和王震宇独立发起的一个艺术项目。从字面上来说,“中国造神”的起名特色和“中国好声音”等“中国abcde”之类的选秀节目非常类似,的确,“选秀”正是本次艺术项目的核心动机和核心符号,发起者丝毫不避讳这一点。同时,“造神”这个略带戏谑揶揄和挑衅的短词在历史文化语境下也暗示着更为复杂的所指。它不仅是一个激烈的动词,暴露出此项目的目标和野心,与此同时更是一个暧昧的形容词,将当代艺术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建构模式一语道破。
崔绍翰在介绍这个项目时说:
我们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废弃的美术馆”,它一面在被持续荒废一面又在荒废中继续重建。参展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有10分钟的个展时间,工作人员会帮助艺术家们来替换作品。观众可以在一个公共空间中现场交换意见、提问以及讨论。我们希望艺术家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艺术家既是海里的驯鲸员,又是鲸鱼本身。他/她需要带领自己前进。

这张“等高线”测绘图很好地说明了两位发起者的意图。曲线图有一种会议记要的即视感。但它同时是逻辑的,并不是一种漫谈。并且整图还充斥着语义模糊的暧昧性,彰显着这几个词汇之间的张力。在几组词汇之间进行充分讨论,这种文化研究式的路径业已成为一种创作思路。经由此图可以考察以下议题:
一:“艺术圈”首先是一个场域(A Site)。
二:场域内部充满起伏不定的“子集”,它们互相影响,彼此合作、竞争、牵扯。
三:这亦是一个生成着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
四:这个生态系统是不稳定的,同时它自身又在拒绝自己的所是(Refuserce Quenous Sommes),我们可以通过想像来建构其他的可能性,以去除现有的权力网络对个体和总体造成的“双重压制”。
王震宇介绍此作品为2017年七月于杭州发起的项目的第一部分。“将以‘艺术家的选秀节目录制现场’作为背景,它是一个实验剧场的形式。”在这个诉求下,项目意在讨论:
一:公共生活是如何被建立的(多少力量牵涉其中,“艺术”如何卷入其中)。人们的公共生活如何被形塑。
二:艺术观点的碰撞与融合。
三:艺术领域新生态环境建立的可能性。
四:艺术家个体的形象塑造。
这个项目计划将要发展成一个类“社会剧团”的组织,一个集结陌生人交流甚至生活的社区(嬉皮士社区),用剧场、活动甚至事件的方式,与各领域志同道合者一同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提炼观点,自由表达。
展示方式:现场演出或者录像放映。
与展览的关系:
此次展览的主题与主要目标为“沟通”。
1.既是香港这片特殊的土地与大陆的沟通。
2.又是两地艺术家之间的沟通。
3.艺术家与公共生活的沟通。
我们将会强化“艺术家选秀节目录制现场”的各种身份建构,并让它们以下人等发声:
评委(评论家、画廊主、策展人)
编导、采访者、主持人
观众
我们希望通过持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人共同来诠释“艺术”这个大命题,建立一个各种身份都参与其中的有关“沟通”与“反思”的特殊场域。不同的声音共同参与讨论艺术家如何介入公共生活,除了传统的展览形式,是否有新的方式可以进行。当这个讨论范围扩大到不同地域的人群(加入香港的艺术家、评论家、画廊主与公众等),便可达到两地的“沟通”目的。营造一个有趣的公共空间。



独立策展人朱其在谈到今天中国的艺术生态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表述:
2000年上海双年展及一系列外围展,算是一次当代艺术最后的回光返照,之后当代艺术基本上在走下坡路,尤其是2005年艺术资本介入后,当代艺术开始商业化,进入了格林伯格称之为“前卫的媚俗”阶段。2005年以后,当代艺术整体上呈强弩之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前卫阵营不复存在……拍卖公司、艺术投资人和经纪人、艺术家形成一个 “做局”的联盟,它们操纵价格发布,影响不明真相的投资人和市场的学术判断…批判和叛逆仍应是核心诉求,当然,批判和叛逆不仅是指政治和社会层面,也可以是艺术史和语言形式上的……艺术界当然存在邪恶,比如体制内的人群结盟,控制美院、画院、美协、美术馆等机构,并控制美术史和教科书……90年代后,当代艺术圈也出现了“邪恶”,比如操纵艺术市场、艺术资本、拍卖会、民营美术馆、双年展、艺博会,甚至编造当代艺术史等……作为一个有待开放的社会,中国与西方当代艺术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当然,中国在政治上仍未走出现代性,因此有关极权主义批判以及现代史的精神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表达的领域,这是中欧当代艺术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地带。
今天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讨论“体制内”或者“体制外”?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制度或者体制——它的含义是多重的。它不仅仅指涉我们所熟知的一系列官方体制(它们同时也是特定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结果),例如画院和美协。还包括舶来的一整套以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收藏家、拍卖机构为核心的商业机制,这样的商业体制是以逐利为核心诉求的,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整套以欧美模式为主导范式的国际化展览体制。此外有一套隐性的准体制模式,即以中国八大美院为辐射中心的院校体制。中国的院校体制和行政管理思维统摄下既得利益者们的圈层文化,使得艺术选拔标准、过程和艺术家的成功模式都带有很大的“宿命”特色。这种准体制与纯市场体制互相钳制,也正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
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人在制度中行动,制度却是人创造的。选择一种制度,往往意味着接受这种制度带来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与此同时承担这种制度带来的结果。换句话说,制度意味着生态系统。例如采用胶片拍摄的时候,会形成一种非常不同的摄影师和拍摄对象的组合。当你用数码拍摄的时候,你会经常去查看屏幕上的相片,结果是你会渐渐失去摄影师与拍摄对象之间的那种紧密联系。那是一种奇妙的联系。这即意味着一种生态系统的选择。
刘国梁的例子可能是一个比较恰切的对比个案。他个人的“陨落”只是举国体制转变落实在个体之上的结果之一。应当将此看作是系统迭代更新的过程,而非看成个人成败的粗暴的阴谋论。它更多意味着产业升级和供需变化。我们今天全部等级森严的美术馆体制都是过去两百年间造神运动中最为激进和前卫力量的结果。与其将“艺术体制”看成是某种本质为权威和压迫性的东西,不如将它看作是动态体系的暂时平衡结果。
一个复杂的世界必须简化,必须剥离掉一些细节,这也是设计的终极作用,这或许也是制度的初衷。在另一种关于制度|生态系统的设想中,美术馆与剧场可能可以作为同谋者,创造一个实验性的奇点。当美术馆作为剧场时,将“表演”融入创作(创作行为本身也是一场表演行动)时,亦即启动艺术创造的“介入”程序,在这里,介入包括“关系”“参与”“对话”“合作”等各种范畴。“关系美学”的核心并不是回归现代主义“自律”审美的古老陈述中,而在于这类艺术形式能够以及必须实现真实的人际互动。形塑着这个世界的其他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能落实于一场虚拟的建构游戏,甚至可以落实于真实的社会活动,获得切实存在的社会效应,换句话说,它可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假设及可能性的路径,也可能成为一场真实的政治对抗。这一切均可游离于双年展和美术馆的体制之外,或者在上述体制中保留有极大的反思成分。这一切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审美愉悦。
“剧场化”一度被指摘为一种倒退(在现代主义意义上的),但这种旗帜鲜明的艺术道德论并不能再能够产生什么新的东西了。纪录片取代了电影。集体性喜剧成为一场公共事件,被注入进公共生活的现身说法里。戏剧指向哲学,观念并不只是一种被架空的产物。正如布莱希特谈到:我的喜剧是一种哲学的戏剧,就这个概念的朴素的意义而言。我想说,它感兴趣的是人们的行为和意见。首先呈现的不是观念的唠叨(这可能正是白立方式作品的集体特色),而是幽默、冲突、分析和过程。一轮无休无止的实验。它的被再现est représentée,是因为它不在场n’est pas présente。
我们生活中所遵守的任何文化惯例,我们所遵守的各种话语逻辑和话语秩序,都不是天然的、确定的,而是任意的,也是经由历史决定的。符号学的观念带来了新的认知方式和认知的可能性。正如罗莎琳克劳斯所言“没有哪种形式能在不懈维持自身的同时还能抵挡得住变化”。
艺术自足领域的神话已经被打破,事实上,形式主义的美学观早已被紧接着格林伯格的下一代人祛魅。艺术实践不仅面向活泼的现实本身,甚至越来越侧重于“观众参与、互动”的面向,它是一个行为、一场事件,它变成一场随即发生、突如其来的冒险:它们是具体的,它们是情境化的(可以暂时用一种粗糙的说法来涵盖它,即艺术的engagement)。在这里,“审美自足”这个专有名词的内涵被扩展了,以朗西埃语境下的歧感为基础的审美路径被一一打开。例如裴开瑞(Chris Berry)将国家|民族的这一研究框架纳入中国电影的研究中,形成了从民族电影到国家|民族电影的范式转变。民族和国家的问题有极大的讨论空间,这本身就是歧感美学的空间。在克莱尔毕晓普的《人造的地狱:参与性艺术和观看者的政治》一书中谈到了参与式艺术的诸多特点,比如“艺术家不再是某一物件的唯一生产者,而是情境的合作者和策划者;有限的、可移动的、可商品化的艺术作品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没有时间起点,不知何时结束的不间断或长期项目;观众从‘观看者’或‘旁观者’转变为‘合作者’和‘参与者’”。“主体身份”的消解本身就是典型的后现代表征,严格的分工体系被瓦解了,渗入和并置是一种常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项目”通常也可以游离于前述诸多体制之“外”,不再囿于画廊、双年展、美术馆这样的标准制度场域,而自然地延伸入社区地文化和政治场域内部:他们之间拥有天然的互洽性。
前卫艺术诞生于大众艺术。换句话说,前卫艺术完全是大众艺术的结果。格林伯格的著名的“二分法”在他最初强有力且毋庸置疑的辩护战打响之后,在他所处的时代里就已经遭受到了猛烈和持久的质疑。“二分法”本身就是一种粗暴的认知结构,最为典型的二分法除了黑人|白人、男人|女人以外,事实上还存在大量的客观|主观和理智|情感这样的二元结构组。例如,人们还是很容易将视觉艺术家想像成是主观的狂热分子,而科学实验和技术从业者恰恰是客观的、中立的、冷静的。这种糟透了二元论竟然长久以来恶毒地嵌入了人们的大脑,实际上,两个领域都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在针对“前卫和庸俗”的个案问题上,托马斯克洛通过大量的论据——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共谋关系——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大众文化是优先的和决定性的,现代主义只是它的后果。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现实的文化语境,决定了前卫艺术的生产和制作方式。
大写的“艺术”在今天应当完全和民众、设计、科技和媒体以及大工业生产紧密相连,按照托马斯克洛的观点,前卫艺术是文化工业的一个研发部门。通过从边缘大众文化中对图像及符号进行精挑细选的挪用,“前卫艺术家们从日益管理花和理性化的社会中寻找出一块保留有生动鲜活生活的社会实践区域。他们将其进行提炼和包装以满足精英阶层和具有自觉意识的观众需要。既有高雅艺术中的某些陈腐过时的规则被强行取缔了,但是种类本身得到了保留和更新——被非精英团体的美学发现更新了”。
反叛成为一种符号,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利用和变卖。这是一个目前不争的事实,但这不能阻止我们去畅想一种“应是”:艺术创作或许没有“推翻”“改造”“颠覆”现实权力体系的直接能力,但它应该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颠覆美学的现有思想基础,以任何形式动摇人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将这类总体性的文化讨论纳入公共讨论的范畴里,不必继承也不可能继承知识分子式的学术表达方法,但在博伊斯的意义上“人人都是艺术家”——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思考和表达,而不至于让所谓“公共讨论”隐匿在虚假的“公共空间”中(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概念产生于自由民主社会。独立并非一定是抗争性的、对立的。独立可以只是一种另类。公共领域不等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或者仅可能成为极小部分学院派的书斋产物。个体被嵌入群体生活中去,公众在闲暇时间里再次体会了团结一致的感觉。尽管很可能是暂时的,是一个浮动的乌托邦。
艺术“界”不再是一场自娱自乐的小范围里的精英活动,尽管在过去它通常都是这样做的——在过去,他们的大众性往往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认知的局限很快在十年的时间里得到迅速改变(如果把十年看成是一段。过去的生态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十足封闭的圈子,并且携带着这个圈子里非常封闭自洽的价值观)。同时,艺术批评还未建立起一个批评框架,艺术批评的“体制化”就已经出现。按照黄专的看法:我们并不处在有利于学术的时代。
高名潞在谈到Culture Industry 的时候,有过三点基本判断:
1、艺术家的职业化,也就是以出售艺术作品为生的艺术家阶层成为艺术生产的主力。
2、艺术作品直接和市场销售挂钩。艺术家成为画廊的雇员,每年领到一笔雇佣金,并定期给画廊交作品,出售分成。这类艺术家在中国是多数,虽然有的价格高的艺术家不选择某一个固定画廊做代理,而是可能在几个画廊同时做部分代理,但性质是一样的。
3、艺术品的生产、市场流通和媒体共谋。任何产品的最高级销售方式是通过广告。没有无广告形象的产品形象,所以,现在也没有无广告的艺术产品(和艺术展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品经营和媒体达成了共谋。现在,在北京和其他城市,艺术杂志汗牛充栋,但是基本上以出售给艺术家和画廊版面为基本经营方式。甚至国家和学院的“学术”杂志也出售版面。市场和媒体(甚至“学术”)的共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我们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并不新鲜却有待被再次讨论的问题:艺术家如何获得独立性。我们要讨论的很可能不是“反体制”这样虚无的伪问题,而是一个“共生”的问题。所有的宏大叙事,判断标准和选拔机制以及成功模式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压倒性的。正如对“艺术”拥有多种角度和多项价值观的判断一样,系统不存在单一指向。
艺术创作的事件化毫无疑问为这样“均等之镜”提供了事实依据。艺术的“事件”逐渐更替着艺术的“物性”或者说它们呈现为一种并存的状态。权力机制和权力结构也被一并改写了——“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我们不可能制造一场幻觉。正如我们不可能发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现实。秩序不过是一种模拟。
玛莎罗斯勒在《观者、买家、画商和制作者:关于受众的思考》里谈到:各个作品类型的观众并不取决于分类而是取决于内容、形式。因此,“观众”是易变的整体,他们的构成并不仅仅依赖于谁在那,而是依赖于你想把这种特定类型的作品带给谁,以及为什么?然而在艺术家与观众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被强调的消极状态,这种状态植根于艺术世界的结构中。
这就是剧场的民主性。没有人可以控制观众看向哪里(虽然在总体上可以决定他们看什么)。从每一个角度观看,看“它”。正如ES Devlin所说“如果你想收藏我做的东西,把它们放进展馆里,它们就失去了原先设计出的价值。它们只有在时光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不同的方式,反射光线与映像。其中又有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台词开着不同的音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