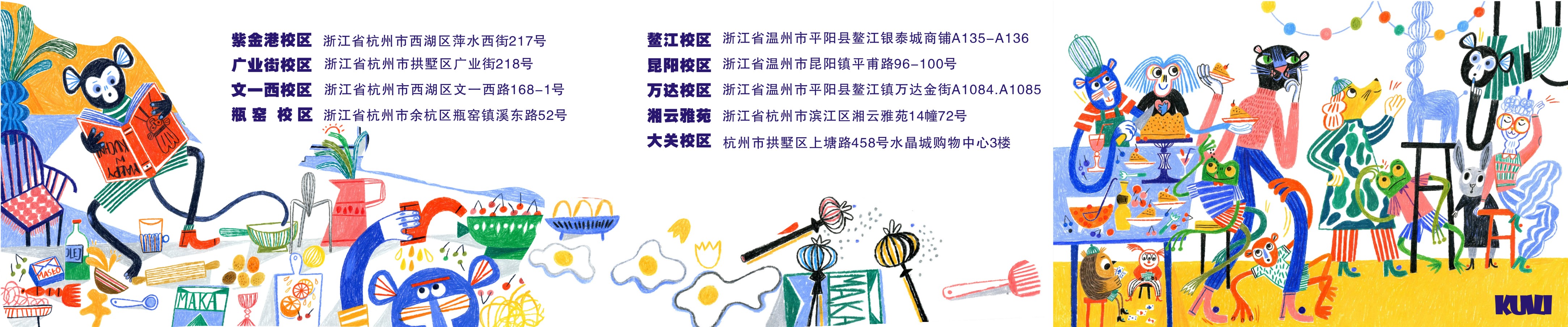陈丹青,平素一向保持短发,衣服的纽扣喜欢一直锁到脖颈——一个也不落下。黑色裤子,黑色皮鞋。洁净的脸庞,好大的眼睛,取来无框的眼镜戴上,粲然一笑:这些年写作,把眼睛搞坏了,这下我看清你了。举止优雅,言语不惊,哪是报纸上白纸黑字、千篇一律、写得分明的那个愤怒甚而偏激的人?媒体为夺眼球,有时难免简单化,画脸只画半张,色彩只用一种。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尚可接受,要不得的是取了筐来,把人往里装,偏又不让争辩。陈丹青道:“各报的形容词,也真看得我心惊肉跳。‘拂袖而去’,那要古人的宽袖这才拂得起来;‘拍案而起’,我与领导谈辞职,彼此笑眯眯,谁也不红脸,国中单位的情面礼数,大家应该知道的。”
《退步集续编》首印十万册,为了配合出版社的宣传,陈丹青需要连轴转,被他自嘲为:接客。
你莫看陈丹青归国以来只是或黯然怀旧,或激愤发言,或批评城市,或笑谈鲁迅;一袭青衫,潇洒走动,风光无限。你又怎么知道作为画家的陈丹青,内心里有着怎样的思量?他的手上雪藏和酝酿着怎样的大作品?陈丹青终究不是做戏给“沉默的大多数”看的人。一个人坐在舞台中央,灯光明晃晃照着,他不见人,人则皆可见他,此番场景哪是这个聪明人的所好!回到画室僻静一角,他最终挥舞的,是手中的画笔,最终留世的,也许更会是他或旧或新的组画。所以,陈丹青所言之“退步”,或者他“退步”的姿势,套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曰:
“退可退,非常退”,大约不错。
关于清华辞职:“我只是逃开,同时叫骂几句”
要说今日的读者,知道陈丹青的,首先是因为“清华教授辞职”事件,其次是因为《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这两本书,再次恐怕才是作为画过《西藏组画》的画家。连陈丹青也疑惑先前哪想到回国教书呢?结果辞职走掉,更不料此事演成社会话题,从此好像欠了前世的债,给舆论逼成“批评专业户”。
自从到了高校教书,陈丹青和许多教授一样,每到招生的季节,必须面对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是政治、外语科目的分数。都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陈丹青感叹:一格一格,全是格呀!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哪里可以看得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普天之下,莫非体制。”陈丹青举了一个例子:当年国学研究院招生,四川一位18岁考生错过报名期限,独来京城求见梁启超与王国维,梁、王居然出见,略略问过来历,梁就想要他,王则引他进里屋考高中语文数理,约一小时半。翌日电话招那学生,即请门房将行李搬入宿舍,上课如仪。1978年,陈丹青自己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结果,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
时间轮转二十余年,英语和政治两课考试的严格限定,使陈丹青四年招不到一个硕士生,他慨然奔走,以无果而终。2003年起意辞职,他说是性格使然,“我顶喜欢尼采一句话:‘服从?No!领导?No!Never’”另外他也觉得年过五十,望见六十,希望重新在画布上扑腾。为此事,陈丹青小心躲着媒体,踌躇数月,终于还是被弄出了巨大的动静来,直到2007年春上走成,辞职这一私人事件已经世间纷扬,让他无处躲藏了。“我只是逃开,同时叫骂几句,就像小时候在弄堂打架,打不过,一路逃一路叫骂,骂给自己听听,也骂给别的弱者听听……”社会上渲染他“退出游戏”的决定,使他在体制内的同行面前感到难为情,甚至愧疚。“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
关于上海:上海是很好的“启蒙老师”
1970年,17岁的陈丹青开始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那时节,勾销上海户口几乎是所有上海人的晴天霹雳。陈丹青茫然离开曾经打架、追逃、斗蟋蟀、爬屋顶的上海石门一路老弄堂。他早年的主题性创作《给毛主席写信》,表现一群知青决意“扎根”农村的心意,而他内心却和成千上万知青一样,盼望回城。
1982年赴纽约定居,2000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执教。去国十八年,户口迂出上海则已经37年了。对上海这座城市,陈丹青说“我浑身上下都是‘上海因子’,虽然不确知那是什么。我的‘处世方式’里布满了上海‘密码’,因为‘布满’,而且是‘密码’,反倒难以举证。”
也许举这样一个例子可以管窥陈丹青的“上海情结”。1993年陈丹青回国探亲,第一件事就是想在上海街头吃碗阳春面,却怎么都没找到。“我心里胃里登时没着没落地,多年梦想的回国剧情才刚开幕,这第一出戏岂不就得泡了汤乱了套了?”幸亏有善解人意的老板娘喔哟一笑:现在没人吃阳春面啦,刚从外国回来吧?好,今天专门为你做一碗!而后,他骑上父亲的“老坦克”自行车,摁着车铃穿弄堂,故意吃几个“弹簧屁股”,听座下的小弹簧“咯吱咯吱”响。
“伤感主义并非仅指心头的思绪,怀旧离不开‘物质’”。喜欢在掌灯时分漫步走过哪条好弄堂走进去游荡的陈丹青,自称“像个鬼”,看人家收回晾出的衣服,门开门关,听弄堂外被隔离的市声。陈丹青说,这是一个50多岁的人的怀旧,个人的一些情感,不能太当真。儿时老屋已经没了,但“家”的感觉还在,“风吹过来,还是上海的风。”
“上海对我非常重要,它是伟大的启蒙教师。”陈丹青说,他无法想象自己出生在别的地方。“上海使我与欧洲不隔,这是‘最大的影响’,可是直到我中年造访伦敦巴黎这才明白。当然,‘油画’是上海于我的影响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想起我是上海人,同时,莫名其妙想起油画。”
“来世投胎,我愿在上海,但不是今天的上海。”陈丹青指的是一个艺术的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岂止是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在亚洲也独执牛耳。中国现代电影史、油画史、音乐史、戏剧史、广告史,和一部分文学史翻译史出版史及所谓文化产业史,差不多就是‘上海史”。在陈丹青的印象里,尤其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文化的上海逐渐凋败了。他认识的几位文艺朋友在九十年代末兴冲冲去上海闯,不久又回到北京。搞文艺的不愿进来了,在上海的人也不愿出去了。而他们那时候都愿意出去,知青一代画家,有多少是从上海出去的?“这些年我招生的时候,很关心有没有上海的学生,请他们举手,结果几乎没有。”这使陈丹青感到怅然。
关于《西藏组画》:未完成的误读之作
1980年1 0月,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展上引起轰动,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逐渐变成一段神话。而在《西藏组画》声名大噪之际,陈丹青离开了中国。此后,他成为中国艺术青年遥远的楷模。2000年,陈丹青回国任教,闪耀的光环使今天的公众很难看清他的真面目。在看过批评家努力建构《西藏组画》的神话文字后,令人释然的是,陈丹青对自己的历史保持着隐忍、理性而诚实的态度。
“我画西藏组画时只想画得和米勒一样,追求我心目中法国式的现实主义。”陈丹青说,“我对西藏既不了解,也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当年我把西藏的视觉经验当作法国绘画的替代,那是一种故意的误读。历史常被误读,西藏组画被神话,也是出于误读吧。”
“作为影响,假如真有影响的话——《西藏组画》是失败的,至少是未完成的。我们因缘际会撞上时代,但没有延续并展开当初的命题,构成坚实的文化脉络,就像第五代导演个个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我们全都来自断层,没有欧洲人的深厚背景与文化准备,九十年代的创作理应超越我们,我想,其中凡是不受影响的家伙,才真有出息,例如艾未未和刘晓东。
上世纪80年代的所有探索是真挚的,但都很粗浅,急就章,它填补了“文革”后的真空。我的《西藏组画》实在太少了,一共七幅,算什么呢?居然至今还是谈资,我有点惊讶,但不感到自豪。
当时我就清醒认识到这一层。1980年10月我毕业留校,1982年元月我就走了。”
关于文学:归国七年出书五本
陈丹青的父亲说,对丹青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他非常自信,送他去学游泳,还没下水,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会游。陈丹青从小就喜欢游泳、音乐、文学、绘画,但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让他学画。陈丹青4岁那年,父亲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丹青难过得整天没说一句话。父亲劝他说“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到公园、马路去画。”一次,父亲在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里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是色彩浓重的油画,原来这是一位侨居意大利的俄国著名画家的杰作《意大利姑娘》,他马上拿回家送给了儿子。丹青花了几个星期临摹,竟画得栩栩如生。
父亲这样评价儿子:在绘画时,丹青没有画高大全的人物;在写文章时,丹青敢讲真话
陈丹青说,他经历了非常匮乏的时代,少年时无书可看,在图书馆“偷”得一本《牛虻》,如获至宝。小学毕业后,他“突然遭遇鲁迅”,那时,《鲁迅全集》成了他唯一可看的书籍,却也让他可以全心全意地只读一个人的著作。14岁时,他替“右派”父亲写申述状,一点都不能出错,于是学会了技巧。40岁时,画画的陈丹青不料自己也作起文章来了,而且一如画画般流畅和充满快感。归国七年来,陈丹青已出了五本书,《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之前的三本是《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和《多余的素材》。出第一本《纽约琐记》时,出版社印了3500册,担心销不掉。2005年出版的《退步集》,如今已是第十三次印刷,达到十一万册,并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且是获奖的10本书中唯一的人文书。2007年4月出版的《退步集续编》,开印就是十万册,有媒体认为是第17届全国书市“唯一亮点”。连陈丹青本人也诧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读者了,“是我招惹还是在被招惹?是如今的言论空间稍许放宽,还是仍旧少得可怜?或许都是原因吧。”